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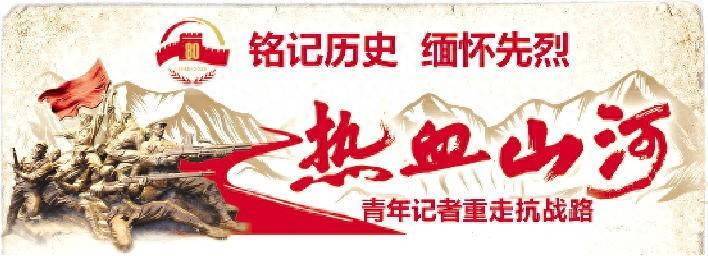

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创建纪念馆内的陈设与雕塑,再现了北海银行开展金融业务的场景。
作为“人民币的雏形”,诞生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北海币成为抗战坚强后盾——
“咱们的票子”打赢根据地货币战争
□ 记者 胡羽
在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创建纪念馆的展柜里,数张泛黄的纸币静静陈列,票面上“北海银行”四个大字历经岁月沧桑,仍清晰可辨。
这些诞生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北海币,被称作“人民币的雏形”,是让老百姓信赖的“咱们的票子”,也曾是支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命脉。北海币版别之多、数量之大、流通范围之广、发行时间之长、币值之稳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红色银行中首屈一指,是“各解放区中最坚挺的货币”。它们无声地记录着一段在战火中捍卫金融主权、建立战时经济秩序的奋斗史。
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麻袋法币,换不来一袋麦子。”抗战初期,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这并非夸张之辞。日伪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直指根据地存亡根基。
彼时,山东各地货币金融状况十分混乱,流通的土杂钞不下数百种。更致命的是,日伪将大量伪造法币投入根据地,疯狂套取物资,导致物价飞涨,“朝是钱,暮成纸”的情况屡见不鲜。敌人妄图从财政、金融上扼住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咽喉,严重威胁着军需供应和抗战根基。
为粉碎敌伪的经济绞索,保障军需、稳定民生、发展经济,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金融机构。1938年,寄托着“南山松不老,北海水长流”寓意的北海银行在烟台掖县开业。尽管次年因日寇进犯一度停业,但其重要作用已被深刻认识。1940年,随着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沂南成立,山东北海银行总行随即组建,成为党领导山东根据地开展货币斗争的核心金融堡垒。
“北海银行在组织章程中明确宣布,成立的目的是‘为繁荣根据地经济,加强对敌金融货币斗争’。”原北海银行沂南办事处老员工蒋文同的回忆,道出了北海银行肩负的核心使命。印发北海币,正是这场斗争的关键武器。从最初的壹元、伍角等小面额纸币,到逐步发行二元、五元直至百元、二百元主币,北海币的发行体系日益完善,流通范围随根据地扩大而不断拓展,发行量稳步增长。
发行新币,是打破敌伪金融枷锁的第一步。但要稳定币值、根治通胀,更需一套治本之策。山东根据地创造性地将币值管理与物资管理紧密结合,以北海币为单一本位币展开货币斗争。
1941年4月,北海银行总行下发《推行新钞宣传大纲》,为北海币的发行与防伪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和省战工会在1942年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对法币打折使用,阻止法币内流及物资外流,逐步禁止法币流通,扩大北海币流通范围,巩固北海币作为山东根据地本位币的地位。
1943年,中共山东分局邀请经济学家薛暮桥来山东帮助开展货币斗争。不同于当时世界上标准的“金本位”货币制和国民党中央的“银本位”货币制,薛暮桥立足革命斗争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物资本位”理论。他指出,货币最根本的保证是物资,掌握物资就掌握了货币斗争主动权。
“‘物资本位’意味着北海币的价值不依赖金银或外汇,而是由政府掌握的粮食、棉花、食盐等重要战略物资作支撑。”沂南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徐庆芳进一步解释,“实践中,根据地工商部门建立起公营商店和合作社网络,大量储备这些物资,并承诺持有北海币可在公营商店按稳定价格购买到这些必需品。这极大增强了北海币的信用,让老百姓坚信它‘值钱’,乐于持有和使用。”这一创举,将货币信用牢牢锚定在根据地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上。
1944年4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宣告日伪币和法币被彻底驱逐出市场,北海币成为根据地唯一流通的本位币。在1945年6月的《山东对敌经济斗争的巨大胜利》报告中,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黎玉指出,“排法”斗争为山东抗日根据地避免了近6亿元法币损失。
物价的稳定是货币斗争成果的直接体现。1945年5月,薛暮桥在全省工商工作会议上说:“伪钞(联币、储币)对本币的比值,从前年七月八月的七元八元跌到现在的一角上下,法币(对本币的比值)亦从一元跌到五分上下。去年伪钞物价上涨了七八倍,而我本币物价在滨海跌落了百分之十,在开始停法排伪的鲁中、鲁南、渤海则跌落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因为货币斗争的胜利,我们已经完全消灭了由于物价飞涨所造成的经济危机。”
草屋里印出抗战“钱袋子”
北海银行的根基,深深扎在根据地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是时任北海银行总行发行科副科长任志明在烽火岁月中刻骨铭心的体悟,更是北海银行于强敌环伺、硝烟弥漫中得以生存壮大的法则。
临沂市沂南县依汶镇大梨峪村,曾经是北海银行总行印钞厂所在地。在口耳相传的历史里,村民们记得1941年农历大年初五天黑后,一支八路军队伍进驻。“背着长枪,手挑肩扛,带着很多箱子。”村民林传富复述着祖辈的记忆,印钞厂就设在林家的宅院里,“堂屋当了办公室,5间西屋放印刷机,是车间。”
印好的北海币,需要依靠手推车、肩挑人抬,源源不断运出山村。大梨峪村村民自发帮助印刷厂将成箱的北海币运往几十里外的双堠镇。肩挑沉重的钞票箱,他们需要翻越三道山岭,涉过两条河流,徒步行走3个多小时。面对运送中的巨额钞票,参与运输的村民始终不为所动,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革命的本钱。
村民们用行动诠释了何谓“依靠”。任志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我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里,厂房就是老百姓腾出的几间草屋。房东经常热情地为印钞厂的同志们烧水做饭,站岗放哨。敌人扫荡时,我们连夜把机器设备埋藏好,把不便埋藏的纸张、票子和黄金托付给可靠的老乡保存收藏起来。在当时那样残酷的环境下,确实没有发生过出卖给敌人的事情,东西也从来没有丢失过。印钞厂在村上工作时间长了,群众也知道一些内容,但没有一人向敌人告过密。”
依靠群众所获得的强大生命力,成为北海银行在战火中拓展的支柱。其分支机构在山东各地相继建立,同样的鱼水情深,也在淄博市临淄区许家村的地下印刷所得以延续。
在许家村一座普通民房下方,保存着一条通往北海银行清河分行地下印刷所的地道。自1940年6月起,印刷机在这隐蔽的地窖中持续工作。地道长约百米,出口通向淄河,是紧急转移的通道。
年逾九旬的许龙章还记得,印钞工作紧张进行,印出的票子由当地可靠的商户前来兑换流通。敌人频繁扫荡,安全如何确保?“村里党员多,二十多个!组织得力,大家非常齐心。敌人多次来袭,我们地下的印钞厂,从未遭受过破坏和损失!”党员的有效组织和全体村民的坚定支持,是这座地下设施得以安全运行的核心保障。
提供场所,承担危险运输,以生命守护秘密……这份在战火中淬炼出的深厚信任,最终凝结于流通中的货币本身,币值稳定、信用牢固的北海币,被根据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咱们的票子”。
从北海币到人民币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海银行肩负的历史使命也随之迎来深刻转变。面对战后连年灾荒的严峻考验,银行迅速调整工作重心,将金融力量集中投向恢复生产、保障民生,只为“不饿死一个人、不荒掉一亩地”。
为解群众燃眉之急,北海银行首先着力于精准的金融支持,贷款优先确保恢复生产所需的资金与物资供应。以1948年秋季的农贷为例,月息仅为一分五厘。这些及时雨般的信贷有效缓解了困境,推动根据地生产活动快速复苏。
与此同时,北海银行还进行了大胆创新。为巩固来之不易的土地改革成果,帮助新获得土地的农民尽快投入耕作,银行创新推出种子贷款、耕牛贷款等实物贷款形式,实行“贷粮还粮、贷物还物”。这一举措极大便利了缺乏生产资料的翻身农民。统计数据显示,仅1948年秋季,北海银行就发放了实物粮食贷款2024.5万公斤,现款贷款(北海币)29.4亿元。贷款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效能的不断提升,为克服严重经济困难、促进农村农业恢复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切实保障了人民生活,也进一步赢得了人民群众对革命政权的信任与拥护。
当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北海银行承担起接收新解放城市官僚资本银行、稳定当地金融物价的重任。印着北海银行字样的货币,跟随华东野战军南下的步伐,驰骋于华东、逐鹿于中原,为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关键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实可靠的金融保障。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推进,新解放的城市越来越多,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为解决华北各解放区货币尚未完全统一的问题,1948年11月25日,经华北、山东、陕甘宁、晋绥政府会商决定,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于1948年12月1日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历史使命圆满完成的北海币逐步退出流通领域。
从开创“物资本位”稳定币值的智慧,到依靠群众、扎根乡村的坚守,北海银行生动诠释了金融为民的理念。这份宝贵的红色金融基因,成为新中国金融事业蓬勃发展的坚实根基与不竭动力。
地窖里印钞票 地面上打游击
□ 记者 胡羽
1941年冬,在沂蒙山区刺骨的冷风中,三名北海银行总行的出纳员牵引着三匹骡子,在崎岖的山路上疾行。在他们身后,敌机的尖啸和炮弹的轰鸣仿佛近在咫尺,这是包围圈正在收紧的信号。影响他们突围速度的不是自己的行囊,而是骡子背上驮着的缴获来的大批法币和黄金,时任北海银行总行行长艾楚南下达了命令:由他们三人带着驮钱的骡子,躲进易守难攻的大崮山隐蔽。
上山后,他们埋藏了法币,将八十多两黄金,贴身藏好。我们最后的阻敌防线眼看就要崩溃,他们又带着金子,转移到敌后的山林里,在找不到村民接应的山头,整整露宿了六天六夜,用意志守护着这份绝不能失落的财富,最终将完好无损的黄金带回了根据地。
类似的故事,在北海银行的发展历程中并不鲜见。在残酷的战争岁月里,北海银行时刻面对着敌人的“扫荡”和破坏。
为了生存,北海银行印钞厂的选址可谓飘忽不定。《北海银行暨鲁西银行货币图录》记载,工作人员常在“可靠的农民家里挖个地窖,或在田野里挖个洞,一旦敌情紧急,便把机器就地埋妥,再把地耕起,一点痕迹不留,人员去打游击”。这种随时转移、隐蔽工作的状态,在1943年6月30日形成的《北海银行北海支行四、五、六三个月工作总结报告》中得到了生动印证。“支行机关则隐蔽在一地坚持工作,白天集合在山头办公,夜间在地洞里分散睡觉。穴居群处,大有原始人之风,以致枪炮之声虽起于邻村,然不妨我算盘声之盈耳也。” 这段“穴居群处”“算盘声盈耳”的描述,也是银行工作人员身处险境却始终保持昂扬斗志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而这穿透硝烟的算盘声背后,浸透了太多年轻的热血。曾在北海银行总行工作的刘惠英,在回忆中刻下了一个永不褪色的名字——庄泳。据刘惠英回忆,庄泳来自莒县大店镇一个地主家庭,身材瘦小,在一次残酷的扫荡中,庄泳不幸落入敌手,壮烈牺牲。在刘惠英的回忆文章中,我们读到这样的锥心之问:“面对凶残的敌人,能够坚定地作出从容就义的抉择,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她?”答案早已镌刻在无数像庄泳这样的北海银行人心中,这股力量就是支撑起整个民族脊梁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
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金融战士们一手紧握枪杆子保家卫国,一手紧握算盘和印版稳定经济,确保了红色金融血脉的畅通,为最终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1943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黎玉在《山东过去政权工作与今后工作方案》中指出:“在敌后困难的条件下,开展银行工作是不容易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全体工人的努力,不管环境如何困难,扫荡如何残酷,在菲薄的待遇、繁重的工作中,日以继夜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从制版到印刷到鉴定到出厂都经过百倍的努力,敌人来了为公忘私地掩藏机器,并开展分散性的游击战争……这些劳动英烈是值得佩服与钦敬的。”
一篇“检讨”社论击破货币谣言
□ 记者 胡羽
1942年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排法”斗争拉开序幕,街头巷尾却弥漫着困惑与不安,各类谣言持续扩散。
“鬼子打击法币,八路也打击法币,这不是帮助鬼子做事吗?”
“这是八路的阴谋,八路准备走,所以大量收买法币!”
“这是土匪行为,等于抢老百姓的钱!”
……
因对政策意义理解不足,加之汉奸特务的恶意挑拨,根据地部分群众出现了思想波动,抵触情绪暗流涌动。
当政策推行遭遇曲解时,1942年7月,《大众日报》发出铿锵之声:“为了粉碎日伪的进攻,保护根据地金融的稳定,山东抗日根据地必迅速‘排法’。即将法币清除出根据地,建立单一北海币市场,增强根据地金融能力,消融日伪币倾销的冲击。”
“敌人对我的货币进攻,不仅是为了捣乱我的货币市场,而且是为了毁灭我根据地,其严重性并不下于军事‘扫荡’。”1942年9月,《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对敌货币斗争的初步检讨》,以“敌我动机对比”的辩证法,使群众看清“排法”斗争绝不是敛财而是救亡。这种认知重构,为北海币取代法币扫清了思想障碍。社论指出,贬低法币价格乃至停止使用法币,正是为了保卫法币,保卫根据地,保卫抗战利益与人民利益,呼吁群众自己不偷用法币,偷卖土产给敌人。同时,社论也深刻反思了工作中的不足。
“东西贱了,日子更好过了,最近山东各根据地都产生了多年未有的好现象。”1944年7月1日,经济学家薛暮桥以大众日报的版面为阵地,发表专文《山东的北海票》。这篇文章系统阐述了北海币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稳定物价、支持生产、保障供给、对抗敌伪金融侵略中的核心作用,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一步论证了独立自主货币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极大地提升了干部、群众对北海币的信心和对金融斗争规律的认识。
“深入宣传动员是一切工作的开路先锋,而正确的货币政策,则是打击敌人货币攻势的主力部队,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与条件,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八十多年前《对敌货币斗争的初步检讨》的结语,至今铿锵有力。当硝烟中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北海币筑牢战时金融防线时,那些承载着政策号令与必胜信念的铅字则织就了一张“信心之网”。
大众新闻记者 胡羽
设计 于海员 马立莹
编辑 黄露玲 纪伟
美港通配资-杠杆炒股官网-中国正规的股票杠杆平台-长沙股票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